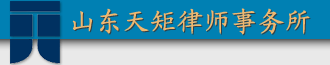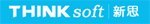诈骗再犯对诈骗罪量刑影响刍议
山东天矩律师事务所 王爱民
序言
笔者接手一诈骗案件:被告人供述其伙同他人先通过网上聊天取得受害人信任,见面后骗色,再以倒卖稀有邮票为由,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骗取多名受害人钱款共计40余万元。但被害人报案又经过查实的只有一起,涉案数额16万元,起诉书所指控的也只有这一次诈骗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作为辩护人,笔者在与承办法官沟通中得知合议庭拟在十年以上对其量刑。根据山东省量刑指导意见,诈骗数额达到3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可以在十年以上量刑。单从诈骗数额上看,被告人不属于数额巨大的情形,而应属于数额较大得情形,量刑区间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但依据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1996解释》),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升格加重处罚,在十年上上处罚。本案被告人确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虽不是累犯,却被诈骗再犯桎梏。照本宣科套用司法解释,该量刑意见似乎无懈可击,但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笔者对诈骗再犯加重处罚不敢苟同,以下为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诈骗再犯 累犯 加重处罚 重复评价
一、对诈骗再犯进行刑事评价的意义
对诈骗再犯进行刑事评价的司法本意是弥补累犯评价再次犯罪的“疏漏”。成立累犯的条件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且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5年内再犯后罪。可见,累犯留下了“刑罚执行完毕5年后”的评价疏漏。当然这个疏漏是立法的有意为之。累犯规定时间条件主要目的在于: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之后设置一定时间的评估期,以便考察前罪的刑罚执行效果,如果犯罪分子在该期限内没有再次犯罪,则说明前罪的刑罚特殊预防目的已经实现,前罪刑罚执行达到预期效果,期限届满对犯罪分子的评估宣告结束,以后再次犯罪的则可能是受到新的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其与前罪的理论联系被认为割断。基于此,对于极长时间之后出现的再犯,其后行为与前罪在司法上应被认定为完全独立,因其再犯对其从重处罚缺乏理论根据。“否则,将会导致犯罪人由于一时之过错,而终生处于评估或者观察期限之中;同时,因为一时之过错,而导致实质上的前科永久存在。”[1]
但是,对于某些特定的犯罪来说,为了表明对其强烈谴责的立法态度,也为了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效应,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不愿意给再次犯罪的评价体系留下“刑罚执行完毕5年之后”这个空档。基于此,《1996解释》规定了诈骗再犯来填补累犯制度的“疏漏”。
诚然,诈骗犯罪作为多发性的侵财犯罪,一直是刑法打击的重点,且诈骗分子多以此为业,顽固不化,再犯概率较高,出于特殊预防的目的,可以将其作为酌定或法定的情节予以从重处罚,但超越法律规定对其加重处罚显然不当。任何制度设计都不能违反刑法的基本原理,盲目对诈骗再犯适用加重处罚看似满足了一时的打击需要,长远看却可能牺牲刑法的基本价值。
二、对诈骗再犯升格量刑、加重处罚,违背累犯从重处罚的量刑理论和立法规定
(一)对诈骗再犯加重处罚违背累犯从重处罚基本法理
累犯与初犯相比,犯罪的客观危害性虽然没有什么区别,但行为人在初次犯罪接受刑罚后再次犯罪,说明其人身危害性大于初犯,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亦造成社会心理秩序的更大破坏,因而在量刑时应当对其从重处罚,这体现了刑法的功利主义考量。但突破法定最高刑,对累犯加重处罚在量刑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犯罪构成是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具体情况也许各异,但只要属于同一类型的犯罪构成,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肯定在该类型的最高危害程度之内,量刑情节都只是针对最高危害程度之内相对于不具有这些情节的行为而言,并不能使具体行为的危害程度高出最高危害程度之内。累犯做为量刑情节之一,当然也只能在行为人所犯之罪的最高危害程度内即法定最高刑内考量,而不能突破法定最高刑加重处罚。个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对具体行为判处刑罚的界限,代表的是个罪的最严重形态,仅仅因为特殊预防的需要,就超越报应的限制,规定对累犯在其所犯之罪的最高刑以上处罚之,不符合我们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量刑理论。[2]因此决不能对累犯加重处罚。
再犯,顾名思义即再次犯罪,而累犯是在再犯的基础上附加了一系列的限制条件,尤其是时间条件后形成的法定制度。累犯是再犯的严格形态,再犯相对于累犯,其人身危害性明显弱于累犯,因此作为量刑情节考量时,其强度当然应弱于累犯。如上所述,既然累犯不能加重处罚是量刑理论的应有之义,举重以明轻,对于再犯更不能加重处罚。显然,对诈骗再犯加重处罚违背了累犯从重处罚基本法理。
(二)对诈骗再犯加重处罚违背刑事基本立法
司法解释是有权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其作出的司法解释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否则该解释无效。无论是79刑法还是97刑法,对于累犯,都规定应对其从重处罚,而《1996解释》规定对诈骗再犯加重处罚显然违背了刑法这一基本法律,作为司法解释其因违法应然无效。且《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犯罪和刑罚只能制定法律。而该司法解释,实际为《刑法》制定了一条刑罚,或者说变相地为《刑法》增加了一条刑罚,超越了解释权限,是一个违法的无效的司法解释,应该予以废止。
三、对诈骗再犯加重处罚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禁止重复评价,是指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重复评价。[3]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既是定罪原则,也是量刑原则,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其一,在某种因素(如行为、结果)已经被评价为一个犯罪的事实根据时,不能再将该因素作为另一个犯罪的事实根据。其二,在某种严重或者恶劣情节已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予以评价时,不能再将该情节作为从重量刑的标准。其三,在某种严重情节已经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予以评价时,不能再将该情节作为在升格的法定刑内从重量刑的根据。如果违反这三个基本要求之一,实际上就会导致同一犯罪受到双重处罚。[4]
在再次犯罪评价体系中,前罪事实能够影响后罪量刑的,除了累犯,诈骗再犯无异是其中的另类。单纯的累犯和诈骗再犯从重处罚并非重复评价,因为前罪事实对后罪的量刑效应以及其所导致的对后罪的从重处罚,是基于前罪的刑罚不足的判断作出的。但是《1996解释》却将刑法确定的从重处罚原则变相为加重处罚,实质上是将行为人已被给予刑事处罚的前诈骗行为又重复在其后行为中进行评价,这显然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对“任何人不因同一犯罪再度受罚”格言的公然违反,应当予以纠正和禁止。
四、《2011解释》对诈骗再犯加重处罚的取舍
针对近年来诈骗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手段,2011年2月21日最高法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2011解释》),该司法解释除了首次对短信诈骗等作出明确规定外,对诈骗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也作出了新的规定。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该解释删除了诈骗再犯这一升格量刑情节,将其回归到法定的或酌定的从重处罚情节。
虽理解有不同,但笔者认为,《2011解释》对诈骗罪量刑情节内容的改变是绝对的改变。且该解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这里的“不一致”,应该包含加重量刑情节本身,所以,原来加重量刑情节中规定而现在没有规定的,应视为与现在不一致,不再成为加重量刑情节,诈骗再犯即属此种情形。司法解释自其适用之日起即具有溯及力,其效力适用于其所属法律的整个施行期间,基于此,诈骗再犯加重处罚应随着《2011解释》的适用寿终正寝。至此,存在于诈骗再犯十多年的司法缺陷得到弥补,司法价值得以彰显。
诈骗罪作为典型侵财案件一直呈多发态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好逸恶劳之徒以诈骗为业,频频作案,二进宫、三进宫等再犯屡见不鲜,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破坏了社会秩序,动摇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显示:在人民法院2010年受理的全部刑事案件中,诈骗犯罪案件数排在第6位。2005年人民法院新收诈骗犯罪案件16345件(含一审、二审、再审)、生效判决人数19685人,2010年这两项数据分别上升至25642件、32284人,诈骗犯罪活动之猖獗可见一斑。
但是,在现代刑事司法领域中,人权保障早已成为与法益保护并驾齐驱的两大价值取向,任何刑法的制度安排都不能过分偏重某一方,任何司法举措更不能逾越人权保障的底线。诈骗犯罪的猖獗不能成为对其再犯加重惩罚的正当、充分理由。以违背刑法基本理论,践踏刑法基本价值为代价换取对某一具体犯罪的暂时压制,显然是荒谬的,也必将得不偿失。为实现刑罚特殊预防之目的,可以将诈骗再犯作为酌定或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予以特别规范,但以司法解释变相加重处罚,笔者认为是错误的。
结束语:
序文中所述案件,因《2011解释》的施行,被告人最终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当然,其中有诈骗数额的影响(《2011解释》将数额特别巨大提至50万),但诈骗再犯加重处罚的废弃功不可没。笔者还了解到之前同一法院基于诈骗再犯对被告人升格加重处罚的另一案件上诉期间亦被二审法院纠正。笔者在为当事人庆幸之时,也倾佩于刑事法官们不受司法惯性束缚,依法、公平做出裁决。
梳理现行司法解释,笔者发现再犯量刑的困惑同样存在于毒品、盗窃等其他犯罪当中。对再犯评价体系的规范和完善,保障刑法基本价值的实现,杜绝司法解释绑架法律,中国的立法者、司法者,包括律师等法律践行者们任重而道远。
注释:
[1]于志刚著:《刑法总则的扩张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2]苏彩霞,《累犯法律后果比较研究:兼顾我国累犯处遇之检讨》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8期。
[3]陈兴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1期。
[4]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